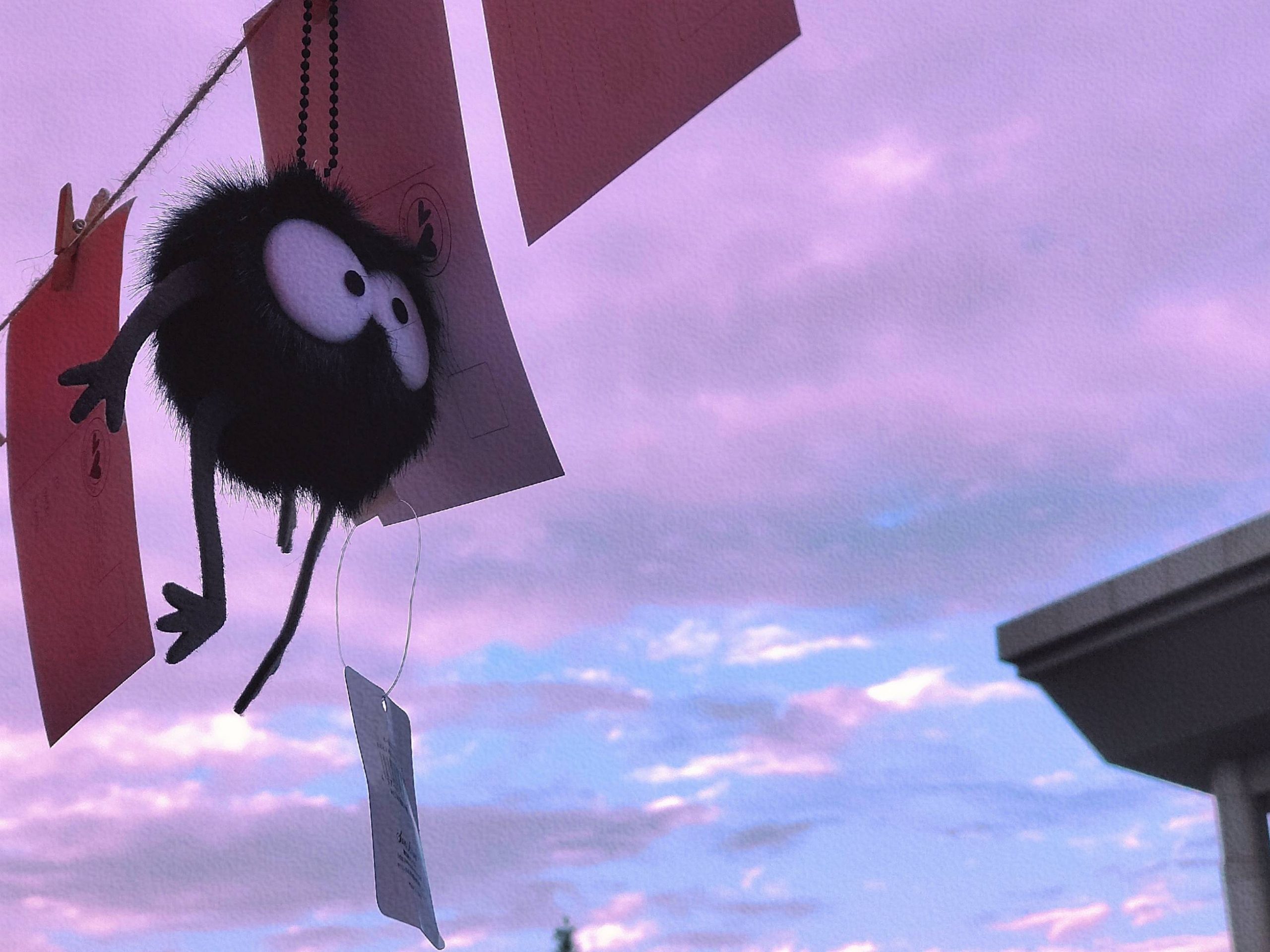这雨已是下了不知多少个时辰,自天亮至现在晌午,期间未曾停过,一中年人倚着家门望向雨中茫茫过客,脸上尽是急切之意,似久候未致之客。许是春秋已高,身子已吃不消漫长的等待,他遂寻了街边一带顶棚的长椅,急行过去,坐入棚下椅上,继续等人。
那块儿瑞士的手表上时分二针已是重合,其所等之人也终究到了,中年人转急为喜,正欲起身,不料一声枪响,胸腔迸发出一股撕裂感,他又倒回了座位上。他的视线已近模糊,看着逐渐化作黑影的客人,嘴上也只吐出含糊的几个字:“为……什么……是……你……”
……
天色已渐趋暗淡,市中心却仍是一派喧闹之景,确实如此,到晚高峰了。杨媛顺着人流,急行于这条与剧场相距不甚远的商业街上。节目终于录完了,一会儿哥哥杨炎会来接她回家。但时下要紧的,是找一个能避雨的店铺,适逢街边开了一家新咖啡厅,招牌上以艺术字书云:咖啡磨坊。伊见状,未曾多想,便推门走了进去。
店内客人不多,加起来也不过三四桌,杨媛坐在靠里的一个较为安静的桌旁,给哥哥发了条消息,便静候侍者前来。
侍者甚是机敏,她方落座,便从前台走了过来,侍者长着锥形脸、尖下巴和一双柔和的桃花眼,鹰钩鼻上架着副细框眼镜,留着背头,若不是那件制服,杨媛更愿相信眼前这男人是某集团公司的阔少。
杨媛方欲开口,不料邻桌传出一低沉男声:“习风,你这里还有吃的吗?有的话给我来点儿。”两人循声看去,只见邻桌坐着一长发男人,他扎着马尾(许是因自来卷的缘故,束着的头发仍显出几分弯曲),下巴较侍者而言平和了些,但仍是有立体感,丹凤眼非但未显出柔和,反倒给人几分寒意的感觉,但老式圆镜框把这种威严削减了一些,略显出几分柔和,却又被镜片反射的灯光削减了大半。待他伸手弹蓝黑色英式西装上的橡皮屑时,杨媛方才看见他手上还握着纸笔。男人又道:“这姑娘的账记在我头上,不用她付了”被唤作习风的侍者回头看向杨媛,问了她想要什么,得知答案后,未等她谈及费用,便转身离开了。
男人放下纸笔,推了推将滑落至鼻尖的眼镜,看着杨媛,表情虽是在笑,却更显几分威严,他道:“这几年里一直都喝这个,你对它是有多深的感情?钱我给你付了,你自己的钱先留着吧,以后花钱的时候可多了去了。”杨媛渐渐缓过神来,正欲推辞,却发觉凭自己对这男人的了解,自己张嘴说一句,恐怕他要回十句,且句句皆有理,遂只得连声道谢,随后,问他:“邵先生怎么在这里?不是已经录完节目一小时了吗?”
男人把推了推正在下滑的眼镜:“我和这家店的店长约好了,等他打烊后陪他打游戏,今天晚上就住这儿了。”
“您认识这家店的店长?”
“嗯,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里公认有两个'老人',一个'老北京',一个'老上海',这俩人一上课就哈欠连天,提前步入退休生活。'老北京'是我,'老上海'就是他,所以我肯定认识他。”男人低头盯着眼前的纸笔,头也不回地应道。
约莫半个小时后,一个被杨媛唤作“哥哥”的年轻男人把她接走了,其余的顾客亦陆续散去了,男人仍坐在原处,停停写写,写写停停,侍者手握饼干,坐到他面前,递给他,问:“翻遍柜子就找到这一包饼干,给,写得怎么样了?”
“能写的都写得差不多了,但缺少几样重要的信息。”墨玦将纸递与习风,纸上开头一行“槍支使用申請書”几个居中写的繁体字清晰可见,趁着墨玦集中注意力去撕饼干包装袋,习风把纸拿过来,扫了一眼:
槍支使用申請書
型號:
槍械數量:
子彈數量:
申請人:“境界”小隊隊員李叔敖、邵辛桐、習風、林夢溪
申請原因:鎮撫使伊諾為火槍所襲,“鏡界”小隊尚未授槍,有殺身之患,此事危若累卵,不可耽擱。
期限:直至任務完成
看罢,习风不禁眉头紧皱:“关键信息一个也没有填啊!申请什么枪,申请多少发子弹都没有写!”“肯定啊!”墨玦撕开了包装袋,拿出一块饼干,正欲往嘴里塞,见他说话,便先回道,“都说了缺少几样重要信息,不然就写出来了。”
正说着,咖啡厅门突然开了,一个黑影闪了进来,迅速把门关上了,把两人吓得迅速起身,墨玦下意识抄起桌上已经空了的咖啡杯。黑影快步走近,待行至灯下,两人才松了口气:是个穿着黑色夹克衫的魁梧男人,夹克衫里面浅蓝色警服的衣领依稀可见。
“你们两个果然在一块儿!”男人操着口东北官话,坐到习风边上,从衣袋里摸出一“中南海”香烟,方叼在嘴上,又忙拿下,问两人,“现在这儿还算是公共场所吗?”
两人摇头,他赶紧把烟塞进嘴里,点上火猛抽一口,道:“局里管的严,我们警队今天下午还一直在会议室里呆着,害得我一口烟也没抽上,快憋死了!”
“没事,叔敖。明天早上烟味就散了,话说那个东西你带过来了吗?”习风问道。叔敖口中连说“有,有。费了好大劲才偷拍到的。”说罢,从手机里找出一张照片,是伊诺的尸检报告,墨玦放大图片,看了个大概,道:“所以警方认为伊诺是被自制枪械打死的?”
叔敖点头道:“没错,警队里那些专家翻遍了现有的资料,甚至还联系了国内外的武器公司,都找不到第二颗6.4mm口径子弹,最后只能归结为是自制枪械。但我之前在满洲军校读书的时候专门学过,6.4mm口径的子弹是大明的一种子弹规格。”
“没错,是手枪的,而且是自卫手枪。”墨玦又推了推眼镜,看来眼镜的螺丝该紧紧了,“我记得我兄弟有一把用这种规格子弹的枪,叛逃那天晚上还拿着。不过在此之前我偷偷用过,准头简直要命——偏差能有一公分。”
叔敖似乎发觉了什么重要的东西,忙问:“你还记得那把枪的型号吗?”
“Z2自卫手枪,一种民用枪,只能装四五发子弹,穿透力不太好,但打人应该够了。”
“所以伊诺是被近距离打死的?”习风听罢,看向叔敖问道。
“现场和伊诺身上发现了火药残余,凶手确实是近距离开的枪。”叔敖点上烟,道,“不过更要命的是,我们发现伊诺的房间全被翻乱了,除了密码保险柜没有打开外,其余东西都乱了,而且伊诺的钱和手机也被拿走了,所以只能定'抢劫致他人死亡'罪或'故意杀人'罪,咱们抓住凶手也不能怎样,相反,恐怕咱们已经暴露了。”
另两人听后,不再言语,许久,墨玦问:“林梦溪知道了吗?”
叔敖点头应道:“在来你们这儿之前我跟她说过了,但她已经搬过家了,新家的地址没有告诉伊诺,现在相对安全。”
“那这样大家都知道。”习风起身,走进柜台里的小屋,那是一间小屋,内设一单人床与一上下铺,及一套折叠桌椅、一块儿落地镜,一床头柜,便别无他物,“今天开始算是进入战争时期了,安全起见,大家今晚都住我这里,我这里应该还没暴露,明天一早大家再走。”
明日,墨玦从床上醒来,屋内二者的鼾声仍如雷贯耳,遂独自穿好衣装,出门回家去了。
……
“'刺客兄弟会'特使觐见!”
墨玦一袭长衫素装迈进太和殿,这屋子,乃至整个紫禁城,自打朱家人为议会夺权后,便没了皇室的踪迹,但唯独今日例外——紫禁城闭城一日,当朝天子正坐龙椅,内阁首辅与诸侍卫列其左右。墨玦至殿下,看了眼阶上供臣子跪安的凳子,忤视圣上,微作欠身,高声道:“'刺客兄弟会'使者邵辛桐见过天子。”
众臣子见这副模样,眼中尽是不满与担忧——不满这后生小子态度傲慢,担忧他今日穿着的氅衫衣袖暗藏短剑火枪,趁机刺杀圣上。然天子未觉不妥,还有几分歉意,缓道:“朕有过,诽'兄弟会'挟朕之爱女宁祎,望邵弟恕罪。”
墨玦皱皱眉,答曰:“此事大可不必多言。”
天子又道:“今郑氏谋反,遣贼至异界欲挟朕之爱女,朕遂置'军政總衙門'以应之,欲请'兄弟会'以助之,不知邵弟意下如何?”
墨玦未作回答,天子遂复言曰:“邵弟信中所诉之求朕皆可满足。”墨玦方点头答道:“愿许驱使。”
翌日上午依规定,墨玦二进紫禁城,经由一警卫引路,进了一间宅院。院门高挂一蓝底金字镶金匾额,上书“大明軍政總衙門”,院内正房门开着,依稀可见里面有人,据说今日的会议便是在此处召开,墨玦遂走了进去。
室内仅有一会议桌与十二三折叠椅,墙上悬有牌匾,由右至左正楷书云“忠君濟民 護國救世”。室内仅有三人,衣着举止截然不同:牌匾下的是一背头男,约莫二十岁初,戴一细金属框眼镜,白衬衫上挂着一胸牌:習風 外科實習生,手握电子笔在平板电脑上勾画,似是白领,然仍有几分稚气;一白肤鹅蛋脸女孩坐在男孩对面,棕色长发披散,一双杏眼前戴着副透明大方框眼镜,上衣长袖白衬衫,下着过膝红裙及白长袜黑高跟鞋,俨然富庶之女,正在笔记本电脑上敲着什么;至于角落里那一袭陆军军礼服的军官,则又是一番样貌:通古斯人的长脸、细长丹凤眼,络腮胡,正目不转睛地瞪着邵辛桐。邵辛桐自知刺客兄弟会与朝廷的账已是一笔勾销了,但此人一脸凶相,实属惹人生厌,遂亦瞪了回去,又将手伸进腰间的枪套里,把自己那用了三代人的卢格P08手枪枪栓拉上来,军官见状,亦是把手放在枪套里,双方就这般僵持着。
十余分钟后,又进入一男人,一袭官服,进屋见二人这般举动,有些惊异,二人见了官员,自知继续僵持不下恐是要出事,便也找地儿坐下准备开会。
“想必诸位也都清楚,军政总衙门在民间一直被唤作'锦衣卫',事实也确实如此,我们做的事也是和锦衣卫一样去搜集情报。”官员落座后,打开文件夹,“不过我们这个小组的任务较其它小组而言,更为特殊,也更为重要。”
见他许久仍未说出重点,军人已作不耐烦之神色,道:“头儿,说来说去,我们到底要干什么?”
官员听罢,嘴角略显上扬,从文件夹里取出面旗子,大红底子,左上角拿金颜料印着一大四小五颗五角星,官员扫视一眼所有人,问:“谁认识这面旗子?”
众人皆摇头否认。
官员又取出一张打印纸,印的是张地图,地图所绘地区之轮廓像只鸡。图表表头印着一行字,这字似汉文,又像日文,尽管已经拿了学士证书的几人也不全都认识: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图。
官员又重复了问题,几人的应答仍是摇头。
“我们的任务就是去这里。”官员道,“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,这是与我们平行的那个世界的'大明'。”
几人听罢,皆斜视他作不可理喻状,军人自扇了一巴掌,但马上就疼得捂起了脸。
官员接继续道:“我能体会到你们的不解,但没办法,我们就是要去这里:这个世界里大明已经亡了几百年了,现在是共和政体,这些我日后自会告诉你们。”
“果然。”邵辛桐低头暗道,“我就知道姓朱的没安好心,找了个二货过来。”
“邵先生有什么想法?”正想着,官员突然开口问他,把他吓了一跳,幸而没有表露出来,他抬头,看着官员,胡乱诌了个问题:“那个世界的政权更替是怎样的?”
官员嘴角略显上扬:“不愧是应天府太学文史院的书生,能第一时间想到这个东西。那个世界的大明在匪顺谋反后为满清夺权,后建立共和体制,现在已经轮到第二个共和体制的政权了。”
这话一出,邵辛桐更觉此人是疯子了——八成是写了小说没落着稿费反被编辑嘲讽一番的“狂人作家”,其余人虽未言语,军人强忍笑意,但从表情上亦能看出,他们也认定此人疯了。
看几人的面容,官员嘴角略显上扬,笑道:“是不是都觉得我疯了?没办法,谁叫另一个'疯子'把我带到过那个地方,不然我也不会'疯言疯语',这些东西改日会告知你们的,若是没有问题,我便讲讲我们的主要任务了。”
军人似是颇有兴趣,亦或是他自始至终都未把这官员当做正常人,双手支着桌子笑问:“什么啊?头儿?”
官员忽做正色,巡视众人,最后将目光落向墨玦,道:“寻回失踪十余年的'宁祎'公主。”
自那以后,“疯子”带着四个“常人”开始各种训练,直到有一天,当他们一如既往地盯着镜子,而镜中图像逐渐扭曲、改变,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世界出现了,他们方知,他们亦是“疯子”了。

 浙公网安备 33011802002150号
浙公网安备 33011802002150号